2015-12-21 来源:党委宣传部 浏览量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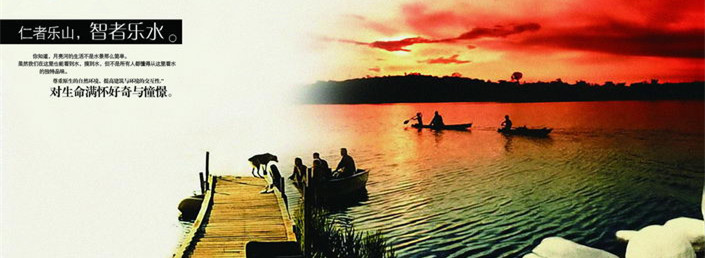
与一个渡口结缘,也许是命定?她在某一时刻,渡你此岸到彼岸。又于某一空间,渡你前世今生。你无法预测亦无力掌控。
伫立黄河南岸,对岸码头的一情一景,尽收眼中。农夫赶猪,毛驴驮草,船夫光脊梁,舵把式叉腿立船头。山崖浑黄,滩涂浑黄,河水浑黄——这是1962年,正值棉花白、柿子红。
也许是阴天。凌晨。一个版本是煤油桶,另一个版本是小木船,母亲永远说不清。我比较相信后者,因为1962年的渡口,摆渡的老船工——老舅拉着母亲的手泪眼婆娑说:“十八年哇,我只说见不着你了!”当年送母亲偷渡的应该也是他。母亲抱着八个月大的姐姐,去灵宝小城与父亲相会,一同逃往西省(家乡人惯把西安叫西省)。这是1944年。据说再迟几天,毛驴车辗着冰层过河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做小商人的父亲不具备对大局势的判断,哪里知道几个月后盘踞小镇八年的倭寇就会滚蛋。
再往前说。他在灵宝一大户人家做私塾先生,她是丫鬟。这段隔河联姻的机缘没有人清楚,可以想象出无数惊艳故事。比如,老爷的赏赐。比如,英雄救美。比如,私奔等。照片上的姥爷儒雅风流,清末遗少的范儿。姥姥圆髻上斜插银簪,宽袖短袄曳地裙,一双缠过又放开的解放脚,面如银月,不施脂粉也会让人凝神。那天姥姥回山西夫家生产,老舅偷偷用小船接她过渡口(大船忌讳)。这该是1908年——四月杏花天。
三代女人的渡河经历故事般惊险、惊艳,命运却被渡口锁牢。107个春秋过去,昔日码头繁华不再,商贾往来旌幡飘摇不再,船夫的号子不再,只有空谷,涛声,暮鸦聒噪,不变。不远处的黄河大桥上车流如潮,摇橹摆渡的衰落、消失是必然。镌刻在女人生命中的印记,是劫数,天命,不可违背。
渡口叫沙窝渡,清以前,曾经叫浢津渡。浢津,辞海里只有一个注释——浢水与黄河交汇处。如今的陌南镇,曾经叫浢津镇,“汉唐重镇”,有过“三十里浢津街”的繁华,古庙香坊,书院祠堂,南北石牌楼,过街戏台,一街的店铺,挂在乡野村妇口边的古语,还有《伐檀》与《硕鼠》。商业文明带来的文化繁荣淹没又复生,或强或弱,或明或暗,化作基因,显现在族群的性格、品质里,代代传承,顽强地让你不可思议。
其实,母亲本可以不过这个渡口,她在甘肃小城平凉已是街道干部,戴着省劳模的大红花进过省城。重新做回农妇的母亲似乎没有抱怨,在西安妇产医院生我包住单间,天天夜里去易俗社看戏,麻将桌上叫羊肉泡馍,穿缎子旗袍逛华清池,十八年的外乡瓢泊,从此复活在不厌其烦却又平静的叙述中。
我向往已久的故乡,由这个渡口开始,一寸一寸,让我从土地庄稼、窑洞水井到村人面上的笑容和深藏于心的或同情或轻视甚至鄙夷中,成熟了一生。故乡,曾经让我爱不能,恨亦不能。
我常常问自己,故乡到底是什么?
与一个人结缘,是命定。他用一纸婚书,就换走了你今生今世的春夏秋冬。在宣传队里,在“忠字舞”、快板剧和蒲州梆子的锣鼓声腔中,我与曾经的同学,做了一家人。初中一个班时不记得我们说过话。他喜欢一位女同学,我则盼着我暗恋的男老师有一天能离婚,然后,等我长大,嫁他。我读到一年半辍学当农民,丈夫拿到毕业证回生产队种地。因为我们几个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能唱能演,所以进了宣传队。白天在沟里竹园挑土培竹,夜晚大队窑洞里排练节目,有任务时露天舞台上演出,是个人人羡慕的活计。工分不少挣,且有粉墨登场的风流。最主要的,是时不时在舞台的各种角色里,忘一回那个真正的自己。
最出彩的是小戏《刘四姐》,演遍了全县甚至邻县的明代、清代戏台。我是女一号——游击队长刘四姐,披一件大队部红旗做的斗篷,腰挎两把丈夫亲手砍削用墨汁染过的木头手枪(这木枪后来成为儿子玩具中的最爱),从戏台上场